走進香港歷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學,見證樹仁大學誕生的故事
更新時間:2025-08-02 17:07:26作者:佚名
走進香港歷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學
央視國際 2007年06月25日 21:40 來源:
專題:CCTV-新聞《新香港故事》
專題:CCTV-新聞“香港回歸十周年”特別報道集錦
消息(新香港故事6月25日播出):點擊看視頻〉〉〉
走進香港歷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學
走進香港歷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學
走進香港歷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學
本集將呈現香港歷史中首所私立學府——香港樹仁大學的誕生歷程。在2006年12月1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宣布樹仁學院晉升為樹仁大學,標志著該校三十余年的辦學艱辛終于開花結果。然而,就在這一刻,學校的創始人鐘期榮女士卻因中風而無法站立,而她的丈夫、著名大律師胡鴻烈則始終守護在她的身邊。香港樹仁學院自1971年創立起,歷經三十五載歲月,直至2006年榮升為香港首所私立大學,其發展歷程全面記錄了香港教育從殖民統治時期過渡至祖國回歸的歷史軌跡。樹仁學院歷經變遷,由起初僅有三百余人的小規模“書院”發展成為一所擁有三千多名師生規模的“大學”;校舍亦從一座三層高的西式洋樓,演變至擁有完備配套設施的永久校舍;從最初被港英政府忽視,到遭受壓制與遺棄,最終贏得香港政府的認可。這一切成就,都離不開胡鴻烈校監和鐘期榮女士傾注畢生精力的努力。然而,樹仁學院的興衰歷程,遠非私人辦學所面臨的艱辛與挑戰所能概括。
詳細內容:
2006年12月19日,我們親臨香港,目睹了一個歷史性的瞬間——香港樹仁大學,這所香港首所私立大學的誕生。
香港樹仁大學慶祝酒會主持人:香港樹仁大學,樹仁大學。

胡鴻烈大律師,這位八十五歲高齡的創校元老,在這一天受到了眾人的熱烈追捧,仿佛英雄一般。三十五載前,他與妻子鐘期榮攜手創立了這所學校,共同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如今,他們的執著終于迎來了碩果,樹仁學院成功晉升為大學,成為香港教育界回歸后的重大盛事。在此之前,樹仁學院長期遭受外界的不屑與輕視。
林偉豪表示,實際上能夠進入樹仁學院,并非一件特別榮耀的事情。對于香港的中學生而言,那是因為它是一種缺乏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的無奈之選。
樹仁學院,這家位于香港的私立學校,曾一度默默無聞,其頒發的文憑在社會上的認可度顯然不及眾多公立大學。許多香港學子,如林偉豪等,正是由于未能如愿進入公立大學,才選擇了在這所學院繼續學業。
林偉豪詢問專業,我自豪地回答:“我學的是新聞。”接著,我大聲補充:“你是在中文大學還是浸會大學?”隨即否定:“都不是,我在樹仁學院。”這樣的回答,正是我典型的反應。
樹仁學院成立于1971年,初始的校園僅擁有八間教室。學院的創始人胡鴻烈及其夫人鐘期榮均出身內地,他們早年赴歐洲深造,均取得了博士學位并抵達香港;胡鴻烈成為香港首位華裔大律師,而他的妻子則在教育領域有所建樹,夫婦二人在各自領域均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在年屆五十之際,他們毅然決然地創建了樹仁學院。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香港地區僅設有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兩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彼時,由前英國殖民政府主導的精英教育政策下,僅有約百分之一點五的香港青年能夠獲得大學教育的機會。
龍子明表示,在那個時期,他迫切渴望閱讀,卻苦于無法實現,內心充滿了不公。隨后,他意外地發現,樹仁學院所提供的大專教育,在當時的1970年代香港,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
三十年前,龍子明已投身社會職場,一個求學機會的降臨讓他倍感珍貴。彼時的樹仁學院,超過八成的學生都采取半工半讀的方式,他們的學業之路異常艱辛。
龍子明表示:“我該如何安排我的學習時間?這個班次從凌晨一點三十開始,一直持續到早上八點,大多數人都對這個班次不感興趣。因此,我特別努力爭取能上這個班。上這個班有什么好處呢?那就是我可以在早上前往樹仁學院上課。”
曾展章表示,由于他每日需攜帶約十五公斤重的皮包,里面裝的是西藥樣品,用于送給醫生以促成生意,再加上晚上閱讀所需的書籍,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一副相當沉重的負擔,日復一日,這些物品都與他形影不離。
張舜堯表示,我們一直是從基層奮斗至上的,與那些歷史悠久、享有盛譽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相比,它們給人的印象總是代表著社會上的精英階層。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由前港英政府實施的精英教育政策,導致眾多人才不愿意投身于香港的基層社會服務,他們中的一部分在完成學業后選擇了出國深造,另一部分則進入了前港英政府的政府部門擔任公職。與此同時,新聞、會計等基礎行業被普遍認為是一項艱辛的工作。
這個教育體系完全模仿了英國的模式,而且并未展現出任何創新之處。
中國文化的根基,對教育的體系、觀念、歷史背景以及理想追求,并無任何關聯。
胡鴻烈大律師的配偶鐘期榮,目睹了香港教育領域的扭曲現象,立志要扭轉這一局面。然而,她和丈夫共同創立的樹仁學院,卻遭到了香港精英教育體系的排斥與輕慢。
2006年12月19日,在一場香港特區政府批準樹仁學院更名為大學的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記者提出了一個頗具挑釁意味的問題,對樹仁學院是否具備成為大學的資格表示了懷疑。

張舜堯表示,觀察到副校長以及全體師生,均察覺到此事氛圍頗為不祥,個人認為這恐怕是對樹仁學院及香港政府的誹謗。當記者提問之際,我立刻想要拿起麥克風回應,然而那位記者卻明確指出問題應向胡校監提問。此外,我觀察到校監當時也打算作出回應。
記者會現場:
胡鴻烈:你這兩個問題都是否。
張舜堯:兩個都是否定,很干脆。
張舜堯表示,他對校監的才智毫無疑慮,畢竟校監曾是一位資深的大律師。他堅信,校監的能力絕對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應付這個問題,但是他肯定出不了這口氣。
記者會現場:
張舜堯提到,在很久以前,曾流傳著一個故事,據說只要樹仁學院同意將學制從四年縮短至三年,它就有望晉升為大學。
張舜堯表示,或許確實如此,在這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里,為了爭取樹仁應得的公正待遇,我們確實做到了團結一致。
自樹仁學院成立之始,便立志要躋身正規大學行列,然而,其正名之路卻充滿了挑戰與困難。
胡鴻烈表示,他不會這么做。他不愿意為了任何一個學生的利益而做出犧牲,因為那些學生的未來非常珍貴。他堅信,四年制的教育要比三年制更加優越。
樹仁學院對港英政府提出的四改三學制持反對意見,認為這種做法偏離了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同時也不符合香港即將回歸祖國的趨勢,未來難以與祖國教育體系相融合。因此,樹仁學院選擇獨自堅持四年制的教育模式,獨自前行。
張舜堯認為這種做法犧牲了學生的素質,因此他們并未予以贊同。最終,其他院校紛紛升級為大學。
在拒絕前港英政府的資金支持不久,他們發現,那些按照新學制要求進行改革的私立學校,很快便陸續晉升為大學。短短十年間,香港的大學數量已經增加到了八所。
張舜堯表示,他后來意識到,樹仁之所以積極爭取,其目的在于爭取到公正的待遇,這正是他努力的原因。

胡鴻烈在創立樹仁學院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放下自己的律師職業。有人比喻,他與妻子仿佛在共同演繹一場雙簧戲,她負責家庭內部事務,而他則在外部奔波,兩人配合得相當融洽。然而,樹仁學院所頒發的學位并未得到社會的認可,這對畢業生而言無疑是一種折磨。為了緩解這一困境,樹仁學院積極尋求與內地及海外高校的合作,分別與美國的三藩市大學和東北大學達成了合作協議,共同培養人才。1985年,樹仁學院攜手北京大學,共同啟動了碩士研究生項目的培養工作,該項目畢業生將獲得雙方合作院校頒發的碩士學位。對于在樹仁學院求學的香港學子來說,他們現在可以暫時放下對學歷的憂慮了!
許賜成表示,我們曾經歷過一段異常時期。在國外,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澳大利亞,都普遍認可我們的學歷證書。然而,在內地,這一認可同樣存在,唯獨香港對此持否定態度,這無疑是對我們的一種不公平對待。
學校成立初期,校舍條件十分簡陋,僅有八間教室可供使用,學生需分批次進行授課。胡鴻烈夫婦主動向政府部門提出申請,希望能夠建設新的校舍。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前港英政府分配給他們的是一塊坡地,依據當時的建筑規范,這塊土地僅能建造兩到三層的高樓。
胡鴻烈表示,當時并不清楚需要鉆探多深,我們確實是在冒險行事。然而,別無選擇,因為這棟房子的樁基工程已經持續了大約八到九年。
胡鴻烈夫婦將他們數十年積累的積蓄悉數投入到了寶馬山斜坡的工程建設中。自那以后,樹仁校舍的建造工程持續了整整二十八年,這對年邁的夫婦所經歷的,是一段既漫長又充滿挑戰的歷程。
胡鴻烈夫婦在回國之前始終拒絕了官方的經濟援助,鑒于辦學所需的費用相當龐大,兩位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極為節儉。
林偉豪提到,校監曾這樣表達,他稱贊我們非常勤奮,正為爭取政府給予我們正名之機而努力。然而,他強調我們的努力并非為了大學,而是為了樹仁。那是我首次了解到學校有這樣的觀念和理念,我們從事的是教育事業,而非僅僅是一所大學。自那之后,我對這所學校有了全新的認識。
盡管他們早年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胡鴻烈和鐘期榮夫婦卻始終以傳承和推廣中國文化為榮。尤其是“樹仁”這一校名,在胡鴻烈看來,“仁”字占據著崇高的位置。
胡鴻烈提到,中國的“仁”不僅涵蓋了愛,還包含諸多其他元素。這種“仁”是具有利他性的,而愛所體現的利他精神,相較于“仁”而言,其影響力較小。在英文字典中,很難找到對“仁”字的解釋。我們當時意識到,“仁”字所代表的是中國精神與道德觀念中最為崇高的境界。因此,在創辦這所學校時,我們的宗旨就是要弘揚“仁”的精神。
胡鴻烈先生在樹仁學院長期擔任校監一職,他給學生留下了溫文爾雅、和藹可親的印象,宛如一位風度翩翩的長者。
林偉豪表示,他覺得我們的校長既英俊又討人喜歡。在香港,許多人奮斗的目標是金錢和名聲。然而,他卻是例外,即便不賦予他名譽,他也能堅守在樹仁學院。在他身上,林偉豪看到了一種精神。
樹仁學子們普遍認為,他們的母校擁有一種獨特的韻味,那是一種宛如家的溫馨氛圍,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嚴肅教育場所。
林偉豪提到,我們經常與其他學校的同學進行交流,甚至去別的學校參觀。我發現那些學校宛如商業機構,高樓林立,人們穿梭其間,彼此似乎互不相識。然而,在樹仁學院,情況截然不同。在這里,無論你遇到誰,都感覺仿佛早已相識,大家都會相互問候,無論是早上還是中午。這種家的氛圍,我覺得是其他地方難以尋覓的。
梁天偉表示,這所學校非常傳統,家長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校長如同一位慈祥的母親,而老師們則像是他的父母。
李娥珍提到,在中秋佳節,她給每位教師發放了月餅,這些月餅被裝進小口袋,掛在宿舍的把手上。這種做法充滿了濃厚的人情味,它所蘊含的起步網校,正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所在。
林偉豪回憶道,校監曾緊緊握住他的手,語氣關切地告訴他:“林偉豪,你需要多加休息。”一個年逾八旬的長者,對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說出這樣的話,令人感到震驚。更令人震撼的是那份深厚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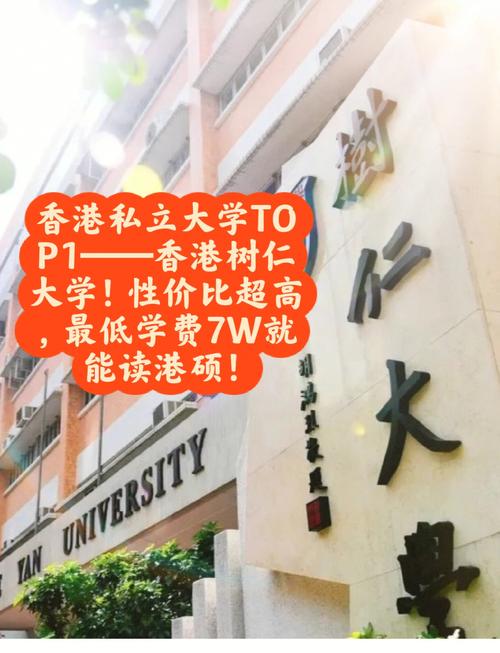
樹仁學院在回歸祖國后,終于獲得了公正的聲譽恢復機會。1999年,香港政府應允對學院進行學術評估,并有意將其提升為大學級別。為此,政府還劃撥了超過四百萬港幣的款項用于學術評審。不過,特區政府對于大學的審批標準極為嚴格,樹仁學院每個系別都必須接受政府細致的評審。對于兩位年事已高的創始人而言,這條正名之路顯得尤為漫長,尤其是對于校長鐘期榮先生,他每日堅守在教學一線。
李娥珍提到,她通常在六點至七點之間離開教室,每天在這個時間點,她都能看到鐘校長從她的辦公室走出。兩人之間有一條長長的走廊,鐘校長從廁所處的燈光開始,逐一熄滅沿途的燈光。這一幕幾乎成了她每日必見的景象。
三十余年的校長生涯中,鐘期榮每日工作時長逾十小時,眾多學生贊譽鐘校長為完美主義者,亦視其為勤勉如僧侶般的人物。
許賜成表示,學校正處于評審階段,她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她每日工作時間長達十二小時以上。我匆忙走進去,只見她坐在沙發上,顯得十分疲憊。我對她說,校長,您這樣真的不行,您必須得好好休息一下。
2001年年末,鐘期榮正忙于為樹仁大學的資格審核事宜四處奔波,然而,由于身心俱疲,他不幸突發中風。
胡鴻烈回憶道,那是在2001年9月18日的中午,我們正在五樓飯堂用餐,我和她同坐一桌,然而就在那時,校長突然中風了。
鐘期榮因中風而倒地,下半身癱瘓,行動不便,說話也顯得吃力。年屆八十的胡鴻烈,從幕后走到了臺前,負責處理學校的日常事務。盡管如此,他依然將校長的名號留給了妻子,這體現了他對學校和妻子的信任。
曾展章表示,她的記憶力有所下降,許多事情她已經無法記起,甚至有時連名字和面孔都會忘記。然而,當我們將她的手輕輕放在她的臉上時,那是一種對她的關懷。盡管她可能無法與你交談,但透過她的眼神,你能感受到她的理解。因此,當你下次見到鐘校長時,只需將她的手放在你的臉上輕輕摩擦,她便能領會到你的關心。
李娥珍伸出她的手,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她的話語雖然微弱,但我還是艱難地聽到了她的聲音,她告訴我,希望我能更多地傳播中國的文化。
經過四年的治療,鐘期榮憑借頑強的毅力香港 大學,站了起來。
李娥珍提到,在中文系的一次課程中,學生們已就坐,我站在教室的窗邊向外望去,目睹了鐘校長在他人攙扶下練習行走的情景。每邁出一步,她都顯得異常艱辛。于是,我示意全班同學起立,一同前往窗邊觀看。實際上,她并非為了個人生活的便利而站立,而是為了給所有人樹立一個榜樣,強調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應當堅持不懈。
林偉豪表示,他心中懷揣著一個夢想,堅守著一份信念,為了實現這個夢想,他愿意舍棄原本較為安逸的生活。這樣的心境,恐怕是極其艱難的。坦白講,他自己也懷疑是否真的擁有這樣的決心。盡管他有夢想,但他也擔憂,未來可能會因為種種原因而放棄追求夢想的勇氣。然而,在我內心深處,我始終銘記著生命中曾出現過兩位長者,他們為追逐夢想而努力。
在充滿挑戰的辦學征途中,樹仁學院必須打造出獨特的教育風格。其高明之舉在于頻繁邀請活躍于香港各行業前沿的管理人士擔任學校的特邀講師。通過這種方式,學生們在學業之余,能夠廣泛投身于社會實踐活動,從而在畢業后更易于被這些特邀講師推薦進入各行各業工作。正因為如此,樹仁學院的畢業生就業率頗高,尤其在新聞媒體等領域,人才濟濟,業績斐然。
張舜堯提到,我們所學專業多為實用性較強的領域,諸如新聞與會計。從某種角度看,這些專業在社會上面臨較大壓力,薪資水平普遍偏低,甚至可以說是勞動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以社會工作為例,需求始終旺盛,然而薪酬卻難以達到較高水平。
胡鴻烈以其堅定的意志和溫文爾雅、謙遜有禮的個性魅力,深深影響著每一位樹仁校友,即便是那些已經畢業二十到三十年之久的學子,也紛紛自發地回到母校,貢獻力量。
張舜堯在一場開幕式上重逢了校監,出乎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立刻認出了我。他邀請我說:“有空多回學校看看。”這讓我深感校監和校長令人動容之處。他并非簡單地說:“你是學校的畢業生,有義務回來學校提供幫助。”他的話語并未讓我們感到自責,反而讓我們感到愧疚。他們的真摯,他們的心靈教育,他們的行為舉止,他們的品德,如同烙印般銘刻在我們每位同學的心中。他未曾明言,卻以行動彰顯,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他對中華文化的自豪,對身為中國人的驕傲。若是他成天向我們灌輸這些觀念,恐怕我們這些同學都會心生抵觸。他并未開口言辭,然而觀察他所完成的各項事務,我認為其中所蘊含的論證力無人能及。

2006年11月13日,鐘期榮校長,這位因行動受限而鮮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教育者,當天卻坐著輪椅,參加了樹仁學院慶祝其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盛大慶典。
龍子明提到香港 大學,在那個夜晚,當校長蒞臨慶祝三十五周年的晚宴之際,她現身的那一刻,我們眾多同學都感動得淚流滿面,對這位長者懷有深厚的情感。
龍子明說,她的心情愉悅,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她了。她主動起身,舉起酒杯。但她的站立時間并不長,自從中風之后,即便是短暫的一會兒也顯得十分吃力。盡管如此,當她站起來舉杯,隨后又坐下時,她的臉上依然洋溢著喜悅。
李娥珍表示,她所代表的是一種精神風貌,而非一所學校,它所體現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我們迫切需要這種精神,我甚至有一個愿望,那就是希望全中國的大學校長都能向我們的鐘校長學習。
李娥珍表示,我們應該向校長學習,這種尊重并非普通意義上的尊敬,而是要體現在向她學習,模仿她的行為上。我常常感嘆,若能回到二十年前,我定能做出更多貢獻。
經過二十八年的不懈努力,到了2005年,樹仁大學文康宿舍樓宣告完工。與此同時,之前已經完工的圖書館大樓和教學樓,共同構成了一個由地下176根樁柱支撐的壯麗奇跡。港人將其比喻為現代版的愚公移山傳說。
胡鴻烈提到,1971年,當學校初創之際,符合年齡可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比例僅有不到兩成。如今,學校需繼續承擔起未來的責任,培育出眾多廣受香港社會好評的建設性人才。這些人才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一國兩制原則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貫徹實施,做出了顯著貢獻。
經過1995年、2001年和2005年的三次嚴格評審,2006年12月19日,樹仁師生終于迎來了他們夢寐以求的這一天——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同意將樹仁學院更名為樹仁大學。在那一天,眾多學生紛紛聚集在學院牌匾之下,期待著留下珍貴的合影,因為這個名字即將成為過去。
林偉豪:那天十九日,我早上八點便起床,如同一位父親期待孩子降臨。我專注地盯著電臺、電視,時刻期待著那個時刻的到來。你可能注意到了,許多同學都身著紅色服裝。其實,我們前一天就已經商定了,約定第二天都要穿紅,因為那確實是一件讓人興奮無比的事情。
林偉豪提到,在十點四十五分這個時間點,他接到了一位同學的來電,這位同學是他的師妹,“我們已經步入大學校園了。”盡管他當時身處家中,但從電話那頭,他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同學在校園中那份激動的情緒。
李國章表示,香港樹仁學院更名為香港樹仁大學恰逢其時,他特別向胡鴻烈校監和鐘期榮校長表示祝賀。自樹仁學院成立至今已走過三十五載,其成就斐然,因此他對樹仁的未來充滿信心。這一變化對香港教育界而言無疑是一大喜事,香港教育統籌局也早已鼓勵私立大學的設立,而樹仁大學作為香港首家私立大學,其誕生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
香港樹仁學院正式更名為香港樹仁大學,這一舉措在香港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作為香港首所私立大學,它的誕生不僅將在緩解當地人才短缺、減輕政府壓力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更將成為一個優秀的示范。
在樹仁學院成功洗清名譽的發布會上,歷經五年中風困擾的鐘期榮校長站上了講臺,發表了演講。
林偉豪表示,在記者會上,校長傾盡全力進行發言。實際上,對于她而言,僅僅出席這次活動就已經十分不易,更別提還要發表講話。坦白講,我完全無法理解校長所表達的內容,一句也聽不明白。然而,那個場合,那顆心,即便難以理解,也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樹仁學院更名為大學的那一天晚上,胡鴻烈與鐘期榮夫婦如常般坐在了電視機前,無人能洞察他們內心的所思所感。那日,他們如愿以償,將心中的理想付諸實踐,他們持之以恒地推廣中華文化,秉持著熾熱的愛國熱情,在回歸之際,得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高度認可。
胡鴻烈表示,我們創立這所學校,旨在弘揚仁愛,培育這種精神。至今,我們已成功實現了這一目標。可以說,正是由于我們確立了正確的辦學宗旨,懷揣著理想,樹仁學院才能穩固立足。這種精神,我認為對于我們國家來說,是一筆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因此,我們之所以命名為樹仁,正是出于對這種精神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