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教被商業排名裹挾,如何重新審視大學的本質與作用?
更新時間:2025-07-23 21:06:44作者:佚名
高等學府作為承載人類文明延續與進步的關鍵組織,其存在的意義不能僅僅被等同于排行榜上的數值比拼。在全球高等教育日益受到商業化排名體系的影響之際,深入思考大學的基本屬性、主要職能及其社會功能,是打造“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學科”不可或缺的過程。
一、大學學術的本質:超越功利的精神共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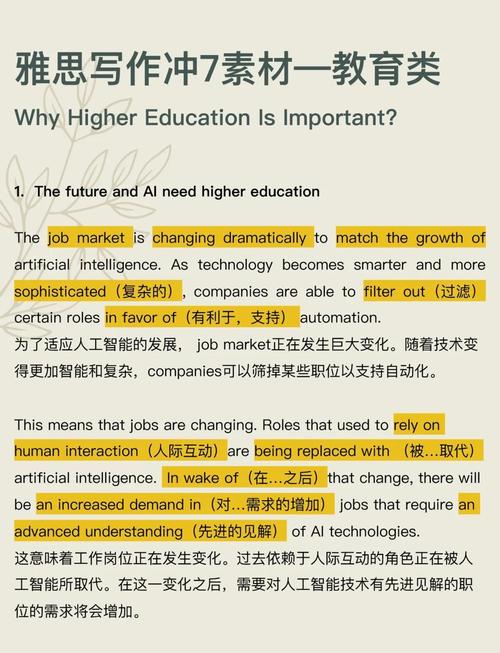
博洛尼亞大學自中世紀起便奠定了其基礎博洛尼亞大學排名,而洪堡則提出了“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理念,這些均揭示了大學的本質——一個致力于探尋真理、傳播智慧的學術團體。在紐曼的《大學的理想》一書中,他明確指出,大學并非僅僅是職業培訓的場所,而是培養智慧的圣地,其核心任務是借助教育手段塑造全面發展的個體。這種精神特質意味著大學的評價標準無法僅通過量化指標全面涵蓋——它包含了學術自由交流所需的呼吸空間,思想碰撞與融合所依賴的包容環境,以及跨學科對話所搭建的開放平臺。這些構成大學精神核心的要素,正是排行榜難以捕捉到的“隱性財富”。
大學若以排名榜上的位置為追求目標,實則將教育簡化為一種可買賣的商品。201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法國科學家塞爾日·阿羅什在2025年的中關村論壇上演講時提到,目前科研環境面臨量化評價的束縛,論文篇數和期刊影響因子取代了同行間的深入評價,而夸大研究成果則成為了一種生存手段。這種異化現象不僅扭曲了知識生產的本質規律,而且削弱了大學作為人類精神寄托的重要地位。
二、功能異化:排行榜扭曲大學的核心職能
教學功能的邊緣化

排行榜過分突出科研成果,迫使教師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論文發表上,而非教學創新。國際知名教育學者菲利普·阿特巴赫于2018年指出,學術界的論文發表量呈爆炸性增長,教師們承受著巨大的發表壓力,這導致了他們更加重視科研而忽視教學。這種以功利為導向的趨勢,直接削弱了大學最核心的人才培養作用,引發了“重視科研、輕視教學”的體制性沖突。學術評價體系的短期化傾向,也加劇了這一問題。
為了提升學校在排名上的位置,高校往往傾向于支持那些周期短、見效快的科研項目,從而壓縮了需要持續投入的基礎學科的發展,這使得長期積累并產生重大成果變得困難;科研工作者為了增加成果數量,往往將一項研究拆分成多個分支進行發表。與此同時博洛尼亞大學排名,排名的壓力導致高校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投資減少,而這些學科恰恰肩負著文明傳承和價值思考的重要使命。這種社會服務的功利傾向。
排行榜使得眾多高校將社會服務轉變為追求“成果轉化率”的數字競賽。以斯坦福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為例,當專利數量成為評價標準,這些高校可能會舍棄那些具有深遠社會價值的公益研究,轉而追求那些商業利益顯著的實用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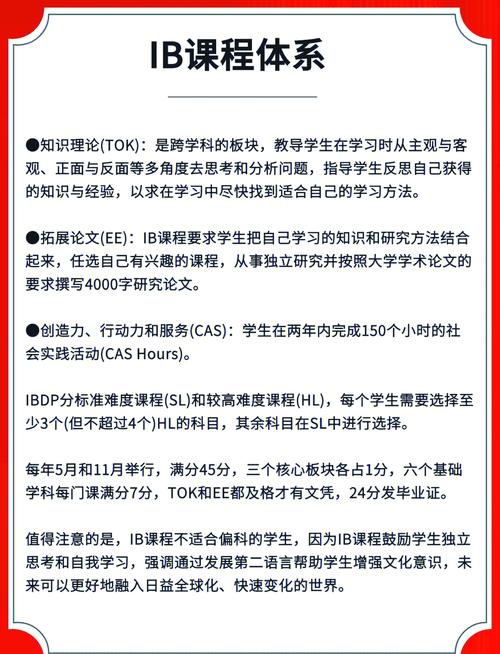
三、公共使命的偏離:大學作為社會良知的擔當
大學的本質意義在于其扮演“社會良知”這一角色時所展現的理性向善的力量。從愛因斯坦對原子彈實用化的抵制,到哈佛學子發起的反越戰運動,大學一直是追求公平正義、捍衛真理的堅實后盾。然而,當大學深陷于排名競爭的漩渦之中時:
四、重構評價體系:回歸大學本質的路徑
建立多維評估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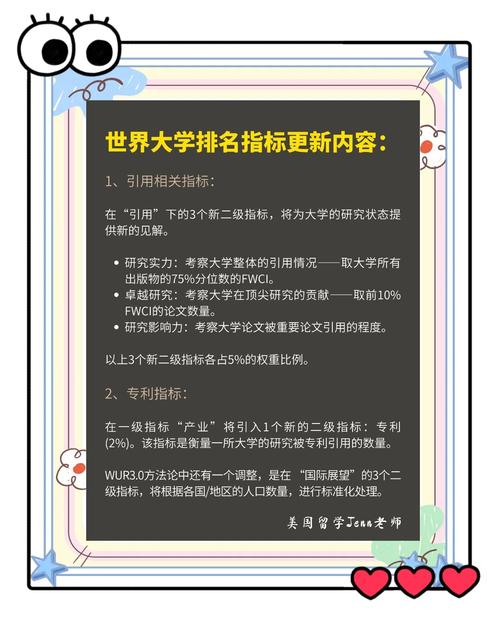
采用“學術貢獻指數”來取代單一的論文數量統計,并將學術影響力、社會創新性、文化傳承意義等多維度因素納入評價標準。例如,將社會效益、開放獲取資源、公眾參與度等要素加入評估范疇。同時,加強同行評審的機制。
為應對學術權力向行政權力轉移的現象,需激活“學術共同體”的功能,借助學科內匿名專家評審機制來確保評價的權威性。同時,對學術權力的尊重并不意味著簡單采納同行投票制度,核心在于依據規則選拔真正的同行,并確保他們能夠合法行使學術權力。此舉旨在重塑對教育質量的認知。
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塑造人的品德與培養人才。在評價體系中,應將學生的辯證思維能力、跨學科融合能力等“隱性素質”納入考量范圍,并借助大數據技術來追蹤學生的認知發展路徑。旨在使學生能夠結合社會現狀、個人能力以及時代背景,進行合理的價值判斷和表達,從而領悟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同時助力他人,提升自我。
大學的尊嚴在于超越排名

往昔歲月起步網校,洪堡大學在十九世紀確立了“以科學為生活準則”的宗旨,西南聯大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堅守著中國學術的命脈,而大學的真正價值從未與排名榜上的位置有所關聯。真正的大學應當是:
大學若能放下對高樓的仰慕,轉而抬頭遙望星空,方有可能成就自身的宏偉;只有擺脫排名的束縛,學校才能重新找回塑造未來的膽識——這種膽識,正是排行榜所無法估量的寶貴精神財富。(李志民,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