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馬斯克成立美國黨,回應(yīng)特朗普驅(qū)逐威脅及沖突始末
更新時間:2025-07-21 15:05:12作者:佚名
7月5日,馬斯克履行了其承諾,正式宣告組建了一個旨在代表大多數(shù)美國中間派民眾的政黨——美國黨。此舉公開對抗了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不久前所提出的驅(qū)逐警告。
7月2日,特朗普透露,他或許會考慮將馬斯克驅(qū)逐出國,同時他還提出,應(yīng)當(dāng)讓英雄去審視英雄,好漢去審察好漢。他主張,馬斯克親自創(chuàng)立的政府效率部門應(yīng)當(dāng)負(fù)責(zé)調(diào)查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術(shù)公司(Space X),并查明它們所獲得的龐大聯(lián)邦補貼,進(jìn)而予以削減。
美國黨的成立宣言,這一事件彰顯了馬斯克對特朗普個人情感上的不滿正逐漸演化為對共和黨整體深深的失望之情。
兩輪沖突
近期發(fā)生的爭執(zhí)構(gòu)成了馬斯克與特朗普之間的第二輪對立,而這兩次沖突的起因均與特朗普視為至寶的“宏大與美麗法案”密切相關(guān)。
6月3日,第一輪沖突爆發(fā),那時馬斯克剛剛離開政府效率部,美國眾議院也剛剛通過了該法案。他在個人社交媒體平臺X上,對法案、特朗普以及共和黨進(jìn)行了強烈的抨擊,指責(zé)該法案“規(guī)模龐大、令人憤慨、充斥著國會利益輸送”,稱之為“令人反感的拼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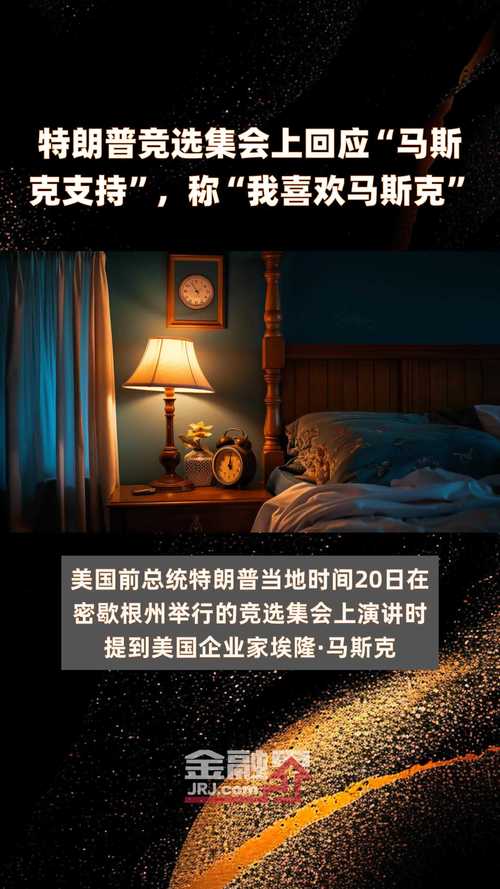
6月5日,馬斯克發(fā)起了一次網(wǎng)絡(luò)投票,詢問選民關(guān)于是否應(yīng)當(dāng)組建一個新的政黨。在獲得了絕大多數(shù)投票者的贊同后,美國黨在X平臺上完成了賬號注冊,并開始頻繁發(fā)布內(nèi)容,旨在為馬斯克競選2028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造勢。
之后,在副總統(tǒng)萬斯以及眾多政治伙伴的協(xié)調(diào)努力下,馬斯克主動展現(xiàn)妥協(xié)之意,移除了若干針對特朗普的批評內(nèi)容,并且公開表達(dá)了對自身某些言論行事的懊悔之情。盡管特朗普在心理上并未完全跨越這一障礙,然而為了“大而美法案”的總體利益,他還是選擇了順勢而為。
然而,雙方的根本分歧難以調(diào)和。“大而美法案”于7月1日在美國參議院獲得通過,隨即引發(fā)了第二輪的沖突。在投票的前夜,馬斯克明確表態(tài),一旦法案得以通過,他將在次日立即宣布成立“美國黨”。果不其然,四天后,馬斯克便開始了這一行動。
核心分歧
特朗普與馬斯克之間的爭議焦點集中在美債議題上。馬斯克與共和黨內(nèi)部極端的財政保守派,即自由黨團,持有相同立場,他們都堅信收支平衡的理念,并堅決倡導(dǎo)實施“有紀(jì)律的預(yù)算管理”,強烈要求減少政府支出。
在競選過程中,特朗普將美國聯(lián)邦政府支出持續(xù)增長作為抨擊拜登的手段之一,然而在債務(wù)議題上,他卻表現(xiàn)得異常寬容。他不僅積極推動兩黨達(dá)成一致意見,以防止政府關(guān)閉,甚至還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即完全廢除債務(wù)上限。
花費的金額、消費的方式,常常是政治家真實理念的直接體現(xiàn)。他們在債務(wù)問題上的觀點截然不同,這種差異凸顯了他們之間截然不同的政治追求。
馬斯克所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小政府”模式,其核心在于全面減少國家對市場和社交領(lǐng)域的干預(yù),旨在為那些象征著人類未來發(fā)展的科技巨頭提供更為廣闊的自由空間,甚至力求創(chuàng)造一個理想的“科技烏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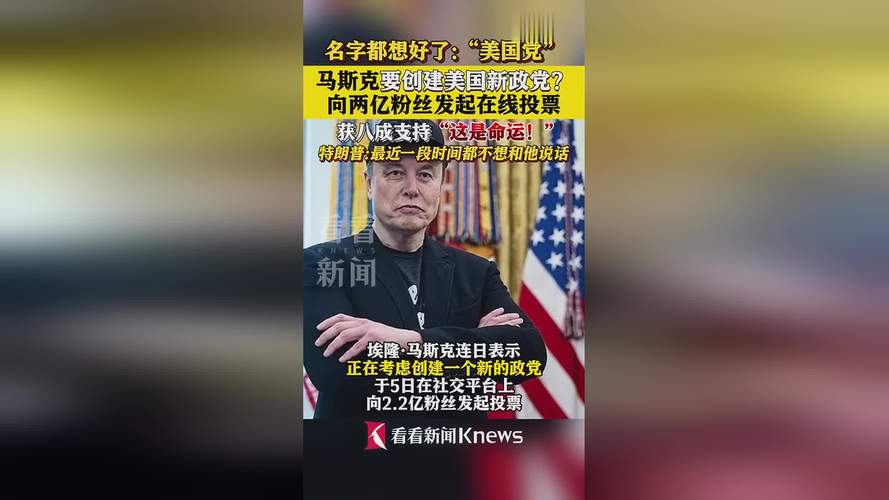
特朗普所追求的是對美國聯(lián)邦政府進(jìn)行改革,使之從推進(jìn)進(jìn)步主義議程的“銳利先鋒”轉(zhuǎn)變?yōu)闃?gòu)建保守主義國家的“堅固屏障”。無論是向因關(guān)稅上漲而遭受損失的農(nóng)場主提供補貼,還是監(jiān)管哈佛大學(xué)以確保教職工的“意識形態(tài)均衡”,這一切都離不開聯(lián)邦政府擁有充足的資金和權(quán)力。
馬斯克對于債務(wù)問題的看法與特朗普相悖,實則是在質(zhì)疑“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能否實現(xiàn)其最終的政治目標(biāo),而這一點對于特朗普來說是無法容忍的。
現(xiàn)在,"大而美法案"演變?yōu)?大而美法"已成為無法改變的現(xiàn)實。即便馬斯克心懷不滿,他也已無法阻止法案的通過,從而對特朗普造成嚴(yán)重的政治打擊。縱使馬斯克擁有足夠的財力去影響包括2026年中期選舉在內(nèi)的關(guān)鍵選舉,但這對于當(dāng)前形勢來說,仍顯得力不從心。
沖突一結(jié)束,馬斯克為了鞏固其龐大的商業(yè)王國,將承受更強烈的妥協(xié)壓力。即便萬斯等政治盟友仍舊愿意為他與特朗普搭建溝通橋梁,馬斯克也需付出更高的代價,才有可能贏得特朗普表面的寬容。
在這場美國保守派內(nèi)部的激烈紛爭中,特朗普顯然是春風(fēng)得意,而馬斯克似乎將面臨一段艱難的時光。在短時間內(nèi)佛羅里達(dá)大學(xué),特朗普有足夠的底氣對馬斯克進(jìn)行嚴(yán)厲的批評,無需擔(dān)心任何后果。
“沉默的大多數(shù)”
至于美國黨,要想構(gòu)成對共和黨的現(xiàn)實威脅,恐怕是長路漫漫。

馬斯克對于將美國黨代表描述為“八成中間派美國人”的看法并非新意。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歷史中,眾多政治人物都自詡為沉默且缺乏組織的“大眾”的代表。這一群體中,既包括了像馬斯克這樣的“局外人”,也包括了那些在美國政壇深耕多年的資深政治家。
尼克松總統(tǒng)自入駐白宮以來,便堅信美國社會內(nèi)有一大群人支持其內(nèi)外政策,為此,他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這一概念,該說法深受后世推崇。
特朗普也曾運用過相近的政治表達(dá),并且憑借這些策略在選舉中取得了顯著成就,成功吸引了原本傾向于民主黨的“鐵銹地帶”工人和低收入白人群體,從而逐步積累了足以徹底重塑共和黨政治影響力的力量。
馬斯克宣布成立美國黨,他很可能真心期望能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外開辟一片新天地,從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馬斯克憑借創(chuàng)辦特斯拉、太空探索技術(shù)公司、收購?fù)铺匾约爸μ乩势遮A得2024年大選等成就,積累了足夠的自信。在“大而美法案”的競爭中遭遇挫折之后,他更傾向于加大在政治領(lǐng)域的投資力度,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其次,盡管美國被視為全球最典型的兩黨制國家,然而在其歷史長河中,并非全然沒有第三黨勢力嶄露頭角的情況。
實際上,共和黨原本便是所謂的“第三黨”。19世紀(jì)50年代,美國國內(nèi)因奴隸制存續(xù)問題引發(fā)的政壇紛爭日益加劇。在這場斗爭中,原先民主黨和輝格黨內(nèi)部反對奴隸制“西進(jìn)”的勢力逐漸聯(lián)合,最終凝聚成共和黨這一新興政黨。

在1856年舉行的美利堅合眾國總統(tǒng)選舉中,共和黨派推舉的約翰·弗里蒙特候選人成功獲得了114票的選舉人支持,而輝格黨派提名的、曾一屆總統(tǒng)身份在身的米勒德·菲爾莫爾候選人,卻僅以馬里蘭州的8票選舉人票為收獲。
此后,歷經(jīng)內(nèi)戰(zhàn)的動蕩歲月,美國政治格局逐漸演變,最終形成了以民主共和兩黨為主的對峙格局,并確立了第三政黨的地位。
美國歷史上的第三黨
縱然馬斯克壯志凌云,美國黨的前景依然不容樂觀。
自1856年以來,歷經(jīng)約170年,盡管美國政黨體系屢次發(fā)生變革,民主共和兩大黨派的對立態(tài)勢卻始終未曾動搖。美國共和黨從邊緣的第三黨躋身主流,這一過程可謂“獨此一次,難以復(fù)制”。在這期間,雖不乏“第三黨”試圖發(fā)起挑戰(zhàn),但它們大多以失敗告終,結(jié)局頗為凄涼。
在歷史長河中,每當(dāng)?shù)谌h派參與選舉,這些黨派合計總共僅有5次獲得了選舉人票,換言之,僅在個別州或數(shù)個州中實現(xiàn)了領(lǐng)先。
1892年,正值美國民粹主義運動風(fēng)起云涌之時,美國民眾黨在總統(tǒng)選舉中成功奪得中西部五州的22張選舉人票;1912年,西奧多·羅斯福領(lǐng)導(dǎo)下的美國進(jìn)步黨在總統(tǒng)選舉中贏得了6個州的88張選舉人票;1924年,羅伯特·拉福萊特領(lǐng)導(dǎo)的新進(jìn)步黨在總統(tǒng)選舉中獲得了威斯康星一州的13張選舉人票;1948年,迪克西民主黨在南方地區(qū)成功贏得四州的39張選舉人票;1968年,喬治·華萊士所領(lǐng)導(dǎo)的美國自主黨在南方五州中贏得了46張選舉人票。
自1968年始,第三黨在總統(tǒng)選舉中的表現(xiàn)持續(xù)下滑。進(jìn)入1992年,該黨候選人便再未在任何一州取得第二名的成績。到了1996年,候選人的得票率更是跌至5%以下。

在現(xiàn)今的美國政治格局中,第三黨派所能達(dá)到的最大影響力,主要體現(xiàn)在關(guān)鍵搖擺州對選票的分散。以2000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為例,綠黨在佛羅里達(dá)州成功吸引了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一部分支持者,這一行為間接幫助了小布什贏得了總統(tǒng)寶座,進(jìn)而入駐白宮。
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即便馬斯克傾注極大的心血去打造“美國黨”,并投入巨額資金,該黨派可能最多也只能成為一個“分票黨”。這一現(xiàn)象背后,存在諸多制度層面的原因,比如美國的“贏者通吃”選舉機制對第三黨的生存與成長構(gòu)成不利,還有民主黨和共和黨通過控制州議會設(shè)置的多重障礙佛羅里達(dá)大學(xué),對第三黨的成長造成了阻礙。
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視。目前,美國國內(nèi)的政治斗爭異常激烈,表面上看是文化保守派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沖突,而實際上則是自由主義放任政策與福利國家理念之間的較量。
美國內(nèi)戰(zhàn)之前,沒有任何政黨將廢除奴隸制作為其核心宗旨,這使得新興的共和黨得以“撿到便宜”。然而,與那時的情況不同,現(xiàn)今美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及其各種主張,基本上已被民主黨和共和黨所采納。這一事實決定了,美國國內(nèi)不存在第三黨能夠崛起的政治空間。
面對激烈的黨內(nèi)斗爭,共和黨內(nèi)部那些對馬斯克抱有同情態(tài)度的成員,相較于與馬斯克聯(lián)手“重塑”特朗普,更傾向于擔(dān)憂在關(guān)鍵選舉中因“票源分散”而敗給民主黨。因此,他們急于勸說馬斯克放棄對美國黨的玩票性質(zhì)的支持,轉(zhuǎn)而回歸共和黨,這個代表著美國保守主義精神的“大家庭”。
免責(zé)聲明
- 澳大利亞留學(xué)好不好?
- 英國有哪些好大學(xué)?
- 美國留學(xué)怎樣省錢?
- 申請留學(xué)需要哪些材料
- 雅思好考嗎?
- 留學(xué)專業(yè)如何選擇
- 那些大學(xué)比較好
- 高考留學(xué)途徑有哪些?
- 哪些大學(xué)有2+2留學(xué)項目
- 美國留學(xué)常見問題
- 英國留學(xué)常見問題
- 澳洲留學(xué)常見問題
- 出國留學(xué)時間該如何規(guī)劃
- 高考后留學(xué)怎么辦?
- 我想留學(xué)
- 藝術(shù)生留學(xué)需注意哪些問題
- 出國留學(xué)怎樣省錢?
- 高考留學(xué)擇校專題
- 2021年留學(xué)政策變化
- 我想留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