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陸大學 馬兵等眾嘉賓對談:經典閱讀的代際偏差與智識魅力?
更新時間:2025-07-20 20:07:11作者:佚名
主持人:
馬兵(評論家,山東大學文學院常務副院長)
對談嘉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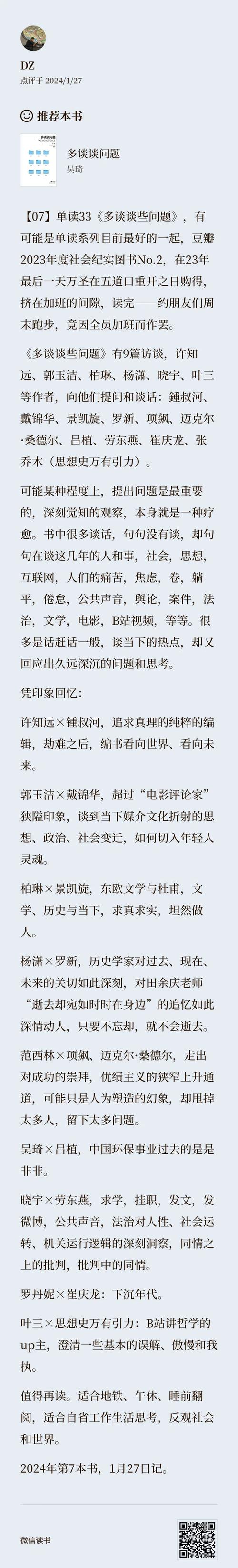
李浩(作家,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劉玉棟(作家,山東作協副主席)
來穎燕(評論家,《上海文學》副主編)
顏煉軍(評論家,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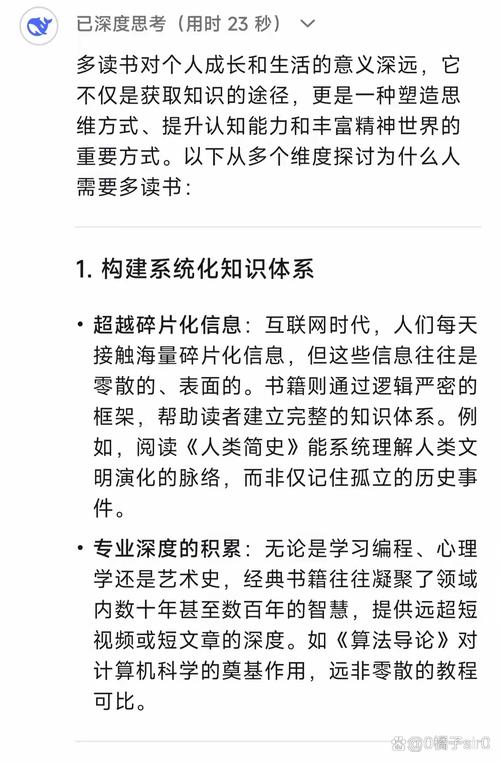
趙月斌(評論家,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王蘇辛(作家)
讀者與屬于自己的經典,是互相激發和成全的共存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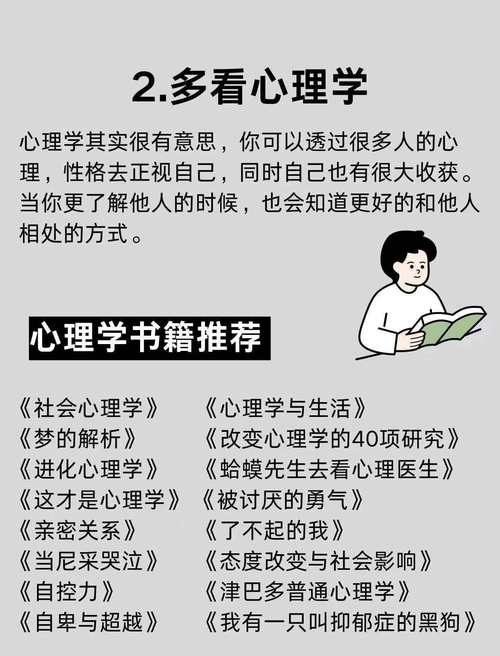
馬兵提到,經典閱讀領域顯現出代際差異,在“五〇后”作家中,他們討論的焦點往往集中在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作品對他們的影響;然而,自“六〇后”作家起,他們探討的議題則更多地轉向了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文學經典對他們的影響。這種現象自然與所處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那么,在您的經典閱讀經歷中,是否也出現了類似的傾向呢?
李浩表示,他對文字中的“智識”情有獨鐘,這讓他感到著迷。他并不沉迷于故事本身,卻對故事中那些曲折展現、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深層內涵情有獨鐘。事實上,他現在認為,自現代以來,優秀的語言是由文字中的智識與作家對藝術的敏銳感知共同塑造而成的。那些引人深思的篇章,其中必然蘊含著多層次、豐富的內涵與曲折,必然流露出意猶未盡之感,必然蘊含著哲理以及哲理難以觸及的微妙之處……在知識層面,現實主義小說常常無法滿足我的求知欲,對日常生活的津津樂道也未能引起我的興趣,這種偏見我并不打算改變,無奈之下,我將帶著它一同走向生命的盡頭。
優秀的小說理應揭示我們習以為常卻未察覺的世界與生活,引導我們進行智慧的較量,并持續地激發我們的靈感與啟迪。然而,這樣的成就往往超出了許多現實主義作品的范疇。然而,我對福克納、海明威、福樓拜等人的現實主義作品,以及門羅、奧康納、海爾曼等人的現實主義作品,抱有極大的喜愛。這些作品給予了我許多教益。而我在小說課的技術講述中,也多以現實主義為基礎。
我仍需著重指出“螺旋上升”這一概念。我堅信,即便歷經數個世紀,“現實主義”仍將作為一種主要潮流存在,然而,它并非我們堅守的純粹現實主義,絕對不是。
來穎燕提到,本雅明在《柏林紀事》中曾言:“當人們打開記憶的扇頁,那些折痕深處的秘密便難以完全揭曉。”我認為,對于很多人來說,閱讀經典作品正如同翻閱這樣一扇記憶之扇。真正的經典作品具有無限延展性,這種延展性與讀者的生活經歷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坐標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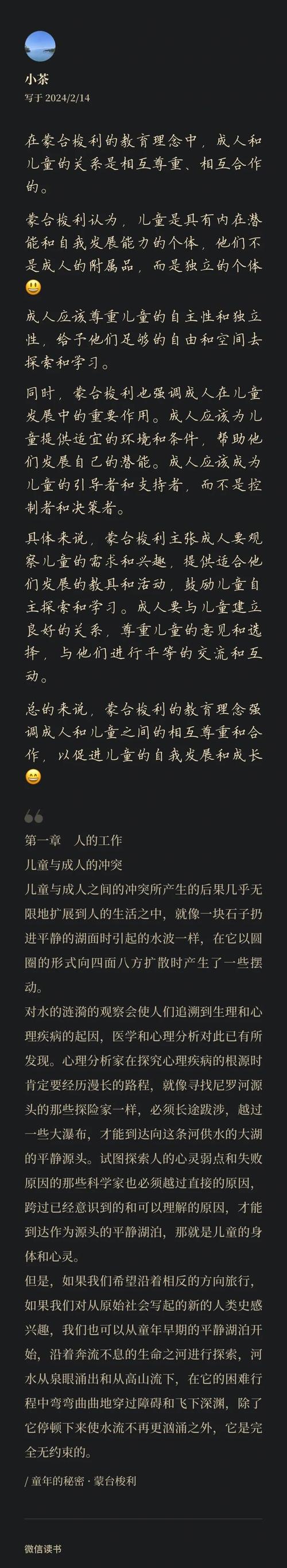
余華曾在挪威奧斯陸大學發表了一次演講,該演講稿后來被賦予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標題——《魯迅是我一生中唯一曾感到不悅的文學家》。然而,若細心聆聽余華的講述,便能領悟到,這“曾不悅”的“曾”字背后蘊含著欲揚先抑的技巧——余華通過自己的過往經歷,巧妙地展現了經典的延展性。在他年少時的記憶中,并無魯迅的作品,僅存有“魯迅”這一名字。在他成為作家之前,他偶然間重新閱讀了魯迅的作品,這才徹底轉變了他對魯迅的看法。由于他當時所經歷的無論是寫作還是人生,都讓他深刻認識到魯迅的作品宛如一片深邃而神秘的森林。正如余華所言:“讀者與作家之間真正的相遇,往往需要等待恰當的時機。”據說,在余華一番話語的觸動下,奧斯陸大學的一位教授步至臺前,感慨道:“你兒時對魯迅的排斥,恰似我兒時對易卜生的反感。”那挺拔的身姿中,蘊含著眾多“我們”的影子奧斯陸大學,成為了這則趣聞中的額外感動。
卡爾維諾在其著作《為什么讀經典》中,詳細闡述了經典的十四個定義。其中,一條與余華、那位教授以及眾多“我們”常陷入的誤區尤為吻合:經典之作,那些我們道聽途說便誤以為熟悉的作品,一旦真正閱讀,反而會愈發感受到其獨特性、出乎意料以及新穎之處。僅僅出于職責或敬意去閱讀經典并無益處,我們應當純粹出于對它們的喜愛去閱讀……未來,你將能辨識出屬于你自己的經典之作。這看似是對經典的一種穩固定義,實則巧妙地將之置于了一種因人而異、相對化的境地。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獨特的經典,經典固然可以提煉出一些普遍的特征,然而在這些共性之外,還存在著各自獨有的特質,這些特質需要不同的人去解讀,去領會,去與之產生共鳴。因此,哈羅德·布魯姆曾言,閱讀莎士比亞的歷程,實則先是我們尋覓莎士比亞,而后靜候莎士比亞的回應——莎士比亞對讀者的理解遠超讀者對他的理解。隨著生活車輪的滾滾向前,我們的內心世界逐漸顯現,而我們最陌生的往往正是自我,正因如此,“莎士比亞”們才會持續喚醒我們內心深處那些被隱藏和被壓抑的元素。讀者與屬于自己的經典,是互相激發和成全的共存項。
王蘇辛表示,他是一位深受現代派小說影響的創作者。無論是現代派美術,還是戈達爾等新浪潮導演的獨特風格,這些視覺和聽覺語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寫作風格。在他看來,文字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因此其結構和構建過程都成為了作品主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奧斯陸大學,并且至關重要。隨著他逐漸認識到內容的重要性超過形式,他的寫作方式也在隨之改變。直面書寫目標,促使內心世界發生轉變,對我而言,這比推動故事情節的進展更具誘惑力;事實上,這正是我所追求的故事魅力。敘述的驅動力源自時間的流逝,而時間,它是唯一能夠賦予生命意義的個體。
馬兵:請問在您精心挑選的閱讀書目中,排在首位的是哪部著作?您為何會挑選這部作品呢?
來穎燕表示,若追溯她早年閱讀的經典之作,毫不猶豫地會提及卡爾維諾精心挑選的《意大利童話》,這部作品幾乎貫穿了她的童年閱讀生涯,至今仍對她有著深遠的影響,從未從她的記憶中消失。與其他童話作品相較,《意大利童話》并不像《安徒生童話》那般充滿了唯美與哀愁,也不像《格林童話》那般深邃且帶有恐怖色彩,然而,它卻蘊含著諸多奇異與難以置信的元素,在我心中留下了雜亂卻充滿野性的美感。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明白,兒時感受到的混亂,實乃一種充滿活力的生命跡象;或許正如托爾金所說,童話故事具備逃離現實、帶來慰藉以及助人恢復的能力,讓我們在奇幻的世界中發現那些平時未曾察覺的過往。直至大學時代,我開始閱讀并深深喜愛卡爾維諾的作品,這才注意到他竟然是《意大利童話》的編纂者。我于是翻開了那泛著黃漬的書頁,尋找他撰寫的序文,那是我年少時常常忽視的內容,然而這次閱讀,其中的一句卻讓我豁然開朗,明白了為何我自幼便對這類故事情有獨鐘——“民間故事通過不斷驗證人間的興衰起伏,在人們逐漸成熟的樸素意識中,為人生歷程提供了深刻的詮釋。這些故事記錄了男男女女們潛在命運的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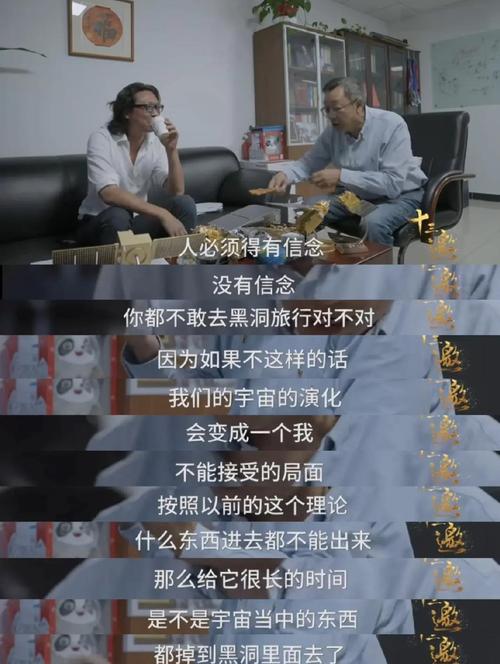
劉玉棟提到,在他珍藏的經典書籍里,《魯迅小說集》無疑是排在最前面的。即便時至今日,我時不時地會翻閱它,挑選其中的幾篇來閱讀。魯迅的這些小說對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每當我閱讀,總能從中汲取到寶貴的啟示,它們就像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庫,令人著迷。魯迅的文風,大家普遍熟悉的是“一株是棗樹,另一株亦是棗樹”,然而,很多人卻未必知曉《孤獨者》里的一句:“整日飄雪,直至夜晚亦未停歇,屋外一片寂靜,靜得仿佛能聽見靜謐本身的聲音。”
馬兵:那最晚的一部呢?又如何理解它的經典性?
李浩表示,他的閱讀進度尚未完成,所謂的“最新的一本”也只能是截止到當前這個時間點的作品。他傾向于將薩爾曼·魯西迪的《午夜的孩子》視為近期閱讀的一部,這部作品充分體現了哈羅德·布魯姆所提出的三個評判標準:審美魅力、認知深度和智慧之光;同時,它也滿足了卡爾維諾對經典作品所設定的多項條件。我之所以將其視為經典,原因如下:首先,它蘊含著充沛的創造力,不僅具備了經典的特質,還展現了獨特的“災變性”,對文學領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其次,薩爾曼·魯西迪所倡導的“復眼式寫作”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手法,使得小說如同枝繁葉茂的百科全書般生機盎然,同時又不失詩意的魅力;再者,他在知識運用上的創新令人嘆為觀止,對“準確”這一概念賦予了全新的內涵;最后,其深度與廣度幾乎無人能及,在我眼中,唯有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可與之相提并論,但薩爾曼·魯西迪的作品似乎更為豐富,更具思想沖擊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真誠與準確之間,薩爾曼·魯西迪常常傾向于站在真誠的立場,這一點對我有著深刻的啟示。
劉玉棟提到,在他珍藏的書籍列表中,最后一本他挑選的是美國作家約翰·威廉斯所著的長篇小說《斯通納》。這部作品與格林的《問題的核心》在精神內涵上有著相似之處。不過,《問題的核心》的故事情節顯得更為直接,而《斯通納》則更多地體現在內在的情感表達。斯通納通過對自己一生的深刻反思和審視,達到了對人性深切的同情與理解。閱讀完畢,那種生命中的空洞、悲傷、凄涼的情感難以消散,仿佛在無聲中聽到了驚雷。在那種沉穩、平靜、清冷的敘述中,它不自覺地讓你的心靈感到驚悚、顫抖,甚至變得清醒。正如其腰封上所描述的:初見故事,再觀經典,三見生活,四見自我。它能夠將真實的自我展現出來,約翰·威廉斯對生命的記錄,是如此的真摯。